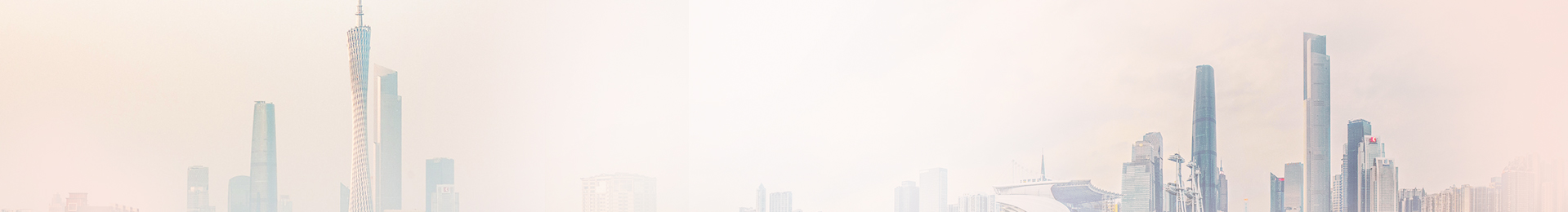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
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
诗社,是诗人为切磋诗艺、吟咏唱和而定期结聚的社团。自唐代以来,诗人们每好结成“吟社”,诗酒酬唱,即今之所谓“雅集”。广州诗人在唐代结社的情况今已无考。见于载籍最早的广州诗社当为南宋名臣、诗人李昴英所结的“吟社”,具体的活动情况亦已不详。
元、明之际,结社的风气甚盛。明李东阳曾记述诗社的活动情况:“元季国初,东南人士重诗社,每一有力者为主,聘诗人为考官,隔岁封题于诸群之能诗者,期以明春集卷,私试开榜次名,仍刻其优者,略如科举之法。”岭南地区最有影响的则是元末的南园诗社。
南园诗社
元朝末年,天下动荡,群雄并起。广州地区尚未遭兵乱,得到暂时安定。元至正十八年(1358),青年诗人孙、王佐与十多位诗友,结社于广州南园抗风轩(今中山图书馆南馆),是为“南园诗社”。青年诗人们欢聚一堂,诗酒酬唱,实在是极一时之盛。五先生的诗中也常提到当时这风雅乐事。南园诗社中的社友,除孙、王佐、李德、黄哲、赵介五先生外,其余如黄楚金、蔡养晦、黄希贡、黄希文、蒲子文、黄原善、赵安中、赵澄、赵讷等,他们的诗作早已散佚无存了。
南园诗社自元末以来对岭南诗坛的影响极大,诗人们以文会友,推动了岭南诗歌的发展。南园诗社已成为岭南诗派的实体,在中国诗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。南园诗社的余韵流风,直到近代依然未绝。
诗人梁有誉是明代诗坛著名的“后七子”之一,登进士第后,任刑部主事。奸臣严嵩父子闻其才名,欲罗致门下,有誉不屑与之多往,遂于嘉靖三十二年(1553),“谢病归,扃门吟哦,罕通宾客。修复粤山旧社,招邀故人,相与发愤千古之事。作《咏怀》十五,诗社中人自以为不及也。”梁有誉所修复的“粤山旧社”,汪宗衍认为即《广东新语》所载的由王渐逵、伦以训创立的“越山诗社”,并“颇疑有誉拙清楼之粤山诗社在越秀山中,与南园在水湄者有别”。而清代学者则多认为梁有誉所修复的是南园诗社。朱彝尊说:“李少偕与梁公实、黎惟敬、欧桢伯、吴兰皋称‘南园后五子’。”乾隆年间,粤中士人陈文藻等辑成《南园后五先生诗》,熊绎组为作序云:“嘉靖年间,复有后五先生欧大任、梁有誉、黎民表、吴旦、李时行者,继南园以结社,振诗学于式微。”檀萃亦云:“迨嘉靖时,社废园荒,欧虞部大任仑山,有《五怀》之作,因与梁比部有誉兰汀、黎参藩民表瑶石、吴刺史旦兰皋、李戎部时行青霞复恢前美,联吟于抗风轩,而‘南园后五先生’称焉。”自经朱彝尊等人品题后,南园后五先生之名,便与南园五先生后先辉映。乾隆二十八年(1763),督粮道京山熊定思答应郡人的请求,建“南园前后五先生词”于抗风轩中。
崇祯十年(1637),礼部右侍郎陈子壮以抗疏得罪下狱,除名放归广州,“复修南国旧社,与广州名流十有二人唱和。”这12人,据欧主遇记载为:陈子壮、陈子升、欧主遇、欧必元、区怀瑞、区怀年、黎遂球、黎邦蠨、黄圣年、黄季恒、僧通岸。并谓“先是吴、越、江、浙、闽中来入社多名流,而期不常会”,可知与会者不止12位,亦不尽是广东籍人。参与修复南国旧社的多为地方官员,张萱曾为作记:“南园旧社,国初岭南五先生之旧。初祀废二百五十余年,今王太父太常虞石王公按粤时,偕黄士明、黄亮垣、韩绪仲、陈集生四太史,陈抑之、邓玄度、刘觐国三观察,高正甫太守,梁幼宁、韩寅仲二明府,韩 孟郁、黎孺旬、黄逢永三孝廉及不佞萱捐资修复者也。”
及至清末,番禺梁鼎芬因弹劾奕山、袁世凯而被斥逐回粤,遂与姚筠、李启隆、沈泽棠、吴道镕、汪兆铨、温肃、黄节等共8人,于辛亥闰六月十七日,聚于抗风轩,重开“后南园诗社”,号召振兴广东诗学。与会者百数十人,姚筠、李启隆作画,梁鼎芬、汪兆诠、黄节等赋诗。梁鼎芬诗云:“十子芳型尚可镌,三忠祠屋旧相连。儒生怀抱关天下,时事销沉过百年。老柳疏疏人照水,山亭隐隐竹成烟。闲来风物当谁赋,长忆陈黎一辈贤。”开会时还举办了一些文化活动,如展览广东历代名家书画,并以《过学海堂有怀阮文达公》、《珠江夜月》等诗题向与会者征诗,由梁鼎芬评阅选拔,各定名次,后来辑成《后南园诗社摘句图》一册,由蒋式芬、梁鼎芬作序刊行。
后南园诗社重开,是历时500多年的南园诗社最后的一次盛会。几个月后,辛亥革命爆发,诗社的活动也停止了。
南园诗社自元末以来,对岭南诗坛影响甚大。南园诗人,标榜汉魏,力追三唐,尤重风骨,对以“雄直之气”著称的岭南诗派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。清代诗人李黼平曾作《南园诗社行》一诗,可作南园诗社史读。
明清广州诗社
明清广州诗人结社,已成习尚。大大小小的诗社,不可胜计。发起人多是一些休致回乡的官吏或地方上的名流。明叶春及说:“国初五先生设咏社于南园,故东粤好辞。缙绅先生解组归,不问家人生产,惟赋诗修岁时之会,故社以续南园。”清乾隆年间,安徽望江人檀萃南游粤东,亲见广州诗社之盛,很有感触地说:“仆客粤三年,居羊城者久,见士大夫好为诗社,写之于花宫、佛院墙壁间皆满。其命题多新巧,为体多七律。每会计费数百金,以谢教于作诗者,第轻重之。流离之英俱得与,不具姓名,以别号为称,有月泉吟社之遗风。”
明嘉靖年间,刑部主事王渐逵、祭酒伦以训在广州越秀山麓结“越山诗社”。王渐逵中进士后,任官不久,即辞归,家居十年,以荐起官言事不报,复乞归,是位高节之士;伦以训是状元伦文叙之子,与兄以谅、弟以诜均中进士,一家科名鼎盛,冠绝一时。以王、伦的声誉志节,自有较大的号召力。越秀山是广州的名胜,故为历代诗人雅集之地。
明万历八年(1580),大学士赵志皋谪官至广州,于城西浮丘建吹笙亭、大雅堂、紫烟楼、晚沐轩诸胜,“开浮丘大社,与粤中士大夫赋诗”。浮丘为西门外一小山,相传为周朝浮丘公得道之所。赵志皋所建的浮丘社,既是祭祀浮丘公和葛洪的祠,也是郡中词人骚客觞咏之所,可算是诗社的雏形。稍后,光禄寺卿郭蓒、王学曾与陈堂、姚光泮、张廷臣、黄志尹、邓时雨、梁士楚、陈履、邓于蕃、袁昌祚、杨瑞云、黄鏊、陈大猷、金节等16人,建立“浮丘诗社”,“以续南园”。
浮丘诗社成为广州文人雅士会聚之所。直至明末崇祯年间,陈子壮、陈子升、黎遂球、区怀瑞、区怀年、高明、黄圣年、梁逵、黎邦蠨、谢长文、曾道唯等复结社于浮丘寺。时广东未乱,士大夫依旧歌舞升平。直至北来的烽火惊破了骚人们的好梦,浮丘诗社也自行消散了。
清康熙二十九年(1690)岭南三家又修复浮丘诗社。诗社虽然重修,但已不常在此进行雅集活动了。
广州城西北有光孝寺,本为三国吴虞翻故宅,历代文人会聚之所。光孝寺西廊为诃林净社,明中叶,梁有誉、黎民表、欧大任诸诗人曾在此结社,以继南园诗社的遗风。明末天启年间,顺德梁元柱以疏劾魏忠贤罢归,复与陈子壮、黎遂球、赵蔰夫、欧必元、李云龙、梁梦阳、戴柱、梁木公重辟“诃林净社”;清初,寺僧愿光又与梁佩兰、周大樽诸词人结社于此。在光孝寺中结诗社的历史长达百年,其影响仅次于南园诗社。明末广州尚有“芳草精舍诗社”,为崇祯末年广州诗人陈虬起与萧奕辅、梁佑逵、黎邦蠨、区怀年所建。诗人“感伤时事,抑郁之气时流露于诗词唱和间”。
明末,陈子壮居于城北兰湖边,因与同好结“兰湖诗社”。清人颜师孔有《兰湖诗社》诗以纪其事:“负郭悟性寺,吟社昔曾开。兰湖汩漪流,应有兰香来。红棉烛法院,青山瞰莲台。胜朝诸大老,此地同徘徊。”“当年陈文忠,园树枕湖隈。花竹宜风月,文藻逾邹枚。”明亡后,“诸老亦殉国,白社化尘埃”,诗社也不复存在了。直到清康熙十九年(1680),梁佩兰与陈恭尹、陶璜、方殿元、吴
文炜、黄河贗等又重修兰湖诗社,又称白莲诗社。时兰湖故地已辟为法性寺,寺中僧人远公、心公亦解诗,法性寺遂成诗人雅集之地,时人编有《法性禅院倡和诗》。
此外,稍有名气的诗社尚有东皋诗社,在广州东门外。崇祯四年(1631),陈子履建东皋草堂,与其弟陈子壮及黎遂球、黄圣年、黎邦蠨、欧主遇、张萱、何吾驺等饮宴其间,唱酬甚密,但尚无诗社之名。直到清初兵燹之后,王之蛟于其地建东皋别业,聘请屈大均、陈恭尹、梁佩兰创“东皋诗社”,“四方投简授诗无虚日,实足抗手南园。”雍正年间,诗人韩海再结诗社于此,与李明辉等唱和。嘉庆三年(1798),羊城诗人又重结东皋诗社。
以上说的越山诗社、浮丘诗社、诃林净社、东皋诗社、兰湖诗社等,在明清两代,多次重修,可见名胜之地对文化活动的影响。
清初,屈大均、陈恭尹、梁佩兰三家,更是热心于集结诗社。顺治年间,梁佩兰、陈恭尹、岑梵则、张穆、陈子升、王邦畿、何绛、梁观等诸人就常集于高俨的两园旅舍唱和。后结为“西园诗社”,参与雅集者尚有程可则、邝日晋、王鸣雷、彭钎、潘元、屈大均、王隼、梁无技及释达津、释愿光等人。屈大均曾记结社的缘起:“慨自申酉变乱以来,士多哀怨,有郁难宣。既皆以蜚遁为怀,不复从事于举业。于是祖述风骚,流连八代,有所感触,一一见诸诗歌。故于尝与同里诸子为西园诗社,以追先达。然时时讨论,亦自各持一端。”可见明代遗民每借社集唱酬,以抒发胸中的郁结,表明自己的心迹,寄托故国之思。但后期社集的诗作,则多流连光景,歌咏岁时风物,较少涉及政治了。
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吴绮“集海内之词人于西禅寺,结‘越台诗社’,至期则宴叙分题”。康熙二十九年(1690),岭南三家又修复广州城西的浮丘诗社。康熙三十五年,黄登于广州东郊黄村辟“探梅诗社”,花时约名流饮酒赋诗其下,延请梁佩兰主持诗社,诗人梁无技、僧成鹫等皆参与其事。
康熙年间,自称为“南塘渔父”的诗人何执,隐居在广州南塘小岛中,闭门著书,不应科举考试。“日与屈翁山、梁药亭、陈元孝、吴山带、王蒲衣辈倡和。又与海幢呈乐和尚、华林铁航和尚、鼎湖契如和尚、尘异、雪木、迹删、心月、敏然等为方外交。四方名士云集,则开‘湖心诗社’,客至不问姓名,觞咏尽欢,或有累月不去者。”湖心诗社是遗民诗人相聚之所。通过雅集活动,诗人互相交流切磋,品评高下,并培育了一批青年诗人,如王隼、梁无技、陈阿平、周大樽、
韩海以及女诗人王瑶湘等,都是在频繁的诗坛活动中成长起来的。还有一些外省入粤的诗人,也参与诗社的组织和活动,如越台诗社就是以“多风力、尚风节、饶风雅”著名的诗人吴绮所倡议的。赵执信、潘耒、严绳孙、周在浚、张尚瑗等一大批游宦诗人,都加入诗社唱和,通过这些创作交流活动,岭南诗家逐渐为中原、江左人士所知,也提高了岭南诗派在全国诗坛中的地位。
随着清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固,天下渐趋“太平”,遗民诗人逝去了,饱经民族动乱之苦的老诗人逝去了。岭南这繁华之地,诗人们还能写些什么呢?康熙末年至乾隆中叶,三四十年间,岭南“风雅中坠”,没有出现杰出的诗人,这也恐怕与当时诗社之多,作诗之滥不无关系。
雍乾年间,广州诗社如林,稍可述者有雍正年间何梦瑶组织的“南香诗社”,参加者有陈世和、罗天尺、苏珥、劳孝舆等人,其中虽没有杰出的诗家,但也有不少颇可一诵的佳作。
乾隆年间,番禺人潘正衡在广州结“常荫轩诗社”,招远近文人雅集,一时称盛。诗人刘彬华曾记述当时广州诗社的活动情况:粤诗社始自南园,继以越山、浮丘、诃林,唱和广,今则无所谓社也。有嗜风雅者为之主,或集名流于园林,或拈题而悬之通衢,能诗者争投以诗,悉自糊名,诗既萃,乃就博雅者品题而甲乙之。甲乙竟,乃求其姓字而榜之,谓之列最;冠军前茅,赠以物,有差,谓之谢教;冠军复踵而行之,谓之继兴。诗社已失去顺治、康熙年间的政治作用,只成为文人雅士吟风弄月的场所了。
嘉庆十七年(1812),黄培芳又在风景优美的白云山麓、濂泉之畔筑起云泉山馆。其《云泉山馆诗》十首之一云:“迹继南园后,山中辟北园。”意图继南园诗社的遗风。参与诗坛活动的除七子之外还有广州及外省入粤的诗人,如黄玉衡、汪铭谦、吴石屏以及曾燠、伊秉绶、汤贻汾、吴嵩梁、魏成宪等。云泉山馆自此便成为广州名胜之地,到来雅集的诗人络绎不绝。
道光年间,谭莹、熊景星、徐荣、徐良琛等又重结西园吟社。成员均为学海堂的学者,学养甚深,所为诗亦颇具功力。
咸丰二年(1852),许祥光在广州太平沙结“袖海楼诗社”。曾以“人日花埭看牡丹”及“羊城元夕灯词”为题,得诗数百首,由张维屏评定甲乙。袖海楼筑珠江边,三层,可容数十人,故一时文人多喜聚于此。
稍后,沈世良、陈澧、谭莹等又在广州结“东堂吟社”,参加者均为一时著名学者,具体的活动已难考了。
诗社的出现,意味着诗人群体的形成。志同道合的诗人有了自己的组织,便有可能在诗坛上发挥更大的影响。直至今天,广州的诗社仍在当代诗坛中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501号
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501号